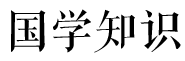孟子天下观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问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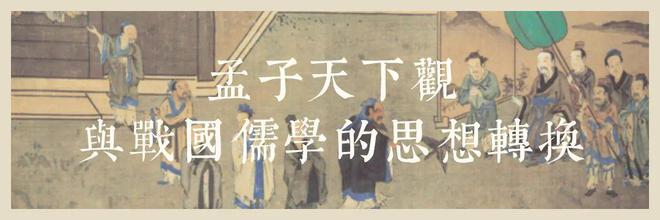
摘 要:孟子天下观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首先,它体现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历史分野;其次,它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和群雄割据的政治现实。孟子天下观也是儒家因应战国时代各种思想挑战的方略之一。它不仅开启了原始儒学的思想转换,不再像孔子那样去倡言“礼乐”,在人性已彻底沉沦的时代里,以“性命”之学构建思孟学派的“性善”说,而且以“仁者无敌”的论断来唤醒统治者,要用仁爱之心去一统天下。孟子天下观是儒者之思,仁者之向往,也是那个大时代里唯一的和最为高尚宏远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孟子;天下观;儒学
一、孟子天下观体现了两个时代的分野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大不相同的。
春秋时代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虽已削弱,但地位尚存。春秋在起自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终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的294年间,诸侯专政,五霸迭兴,他们皆利用周室的名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各取所需,称霸天下。然而,孔子对于春秋霸主的评价并不都是消极的,而是有所肯定的,如孔子对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作为,就持肯定态度。《论语·宪问》中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孔子的肯定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尊王攘夷是切合那个时代政治现实的一种举动,虽不完全符合周礼的尊尊之道,但却维护了王室的尊严,安定了天下,造福苍生而泽被后世。其二,它捍卫了华夏文明的正统,阻止了“以夷变夏”的文明倒退,挽救了华夏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避免了落后民族的入侵。因而,这一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和伦理层面及其传统要求的标准和高度。其三,孔子认为不能以普通人的政治伦理标准,来要求像管仲这样的大人物,对于政治家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要看他能否舒缓与化解天下之困厄,带领国民进入一个全新而光明境地的能力与贡献。而孔子对管仲的品评标准即是如此。
在春秋时代不断变乱的政治动荡中,孔子的这种品评标准具有划时代的思想高度,那就是以尊重政治现状为前提的思想意识。原因在于从西周后期以至于春秋时代,“国人”和平民阶层的崛起,西周传统的宗法政治日渐衰微,随之而来的是周天子地位的不断弱化。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历史趋势的推动,才证明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与时俱进的,或者说他不局限于一成不变的某种固定思维程式,而是力求切合于时代转换后的客观需要,经得起春秋时代政治实践的严酷检验,以最终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为目的。
孔子经常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其实这只是他的学术态度,并不能代表他的政治立场,事实证明孔子在政治思想上绝不是保守的。童书业先生在其《春秋左传研究》中就指出,孔子是春秋时代“贵族改良派”的代表人物3,孔子为鲁司寇兼摄相事时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以维护传统的姿态大胆改革,“堕三都”以还政于君,斥季氏“八佾舞于庭”而正礼乐之宜,虽为“复礼”之举,然其追求政治秩序之井然有序,以国民福祉为奋斗目的的本意,则无可置疑。仅从孔子的政治目的和其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奋斗精神来看,他的选择并不是一味去迎合现实,而是力求达到一种理想政治的落实,因为要实现理想预设的目的,是需要有永不停歇的改革动力来支撑的。诚如孔子自己所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4这种“克己”“尽己”的不懈追求精神,勇于道义担当,当仁不让的奋斗实践,在孔子那里,实为儒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的崇高理想信念的体现。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则不同,这是一个失去了天下共主的乱世,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在这个时代里,战国七雄各自称王,而“王”号本质上已大大地贬值了。如果说春秋时期的“王”,即周天子还有和平一统、天下安宁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战国诸“王”则是动乱与争霸的象征孔子的政治思想内容,是将人们带到了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6的无比黑暗岁月的罪魁祸首。因之,孟子的生存环境显然已不如孔子的生存环境,孟子面对的社会现实已经和孔子面对的春秋时代迥然相异。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民生窘困,朝不保夕,生灵涂炭的悲惨世界里,已无需“尊王攘夷”的呐喊,更无需“克己复礼”的匡正。同时,一切以安天下为目的,以孔子原始儒学所提倡的理想道德为归依的政治伦理,以及由此而确立的等级规范、王道礼制和政治秩序都已荡然无存了。诚如汉代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赵歧在他的《孟子题辞》中所描述的那样,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逢“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7正因为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和春秋时期已全然不同,孔子在春秋时代所提倡的诸多儒家思想主张,鲜有能在战国时代推行的可能性。所以,孟子面临的问题和孔子面临的问题已大不相同,如果照搬孔子的思想和经验,不仅难以契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不能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于是,孟子以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游于诸侯”,奔走呼号,勇于干政而不计其成败得失。孟子的所有斗争和付出,正是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伟大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时代与现实的变异,使孟子不再指责“礼崩乐坏”的现状,亦不再强调“克己复礼”的重要,更不提“必也正名”的关键,而是在一个没有天下共主的时代,一个失去了传统政治规范的时代,去寻找一种缓解诸多矛盾的治世良方。孟子已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取得医治乱世的良方,就必须打破战国诸王各自控驭的所谓国家利益的藩篱,其视野必须超乎其上,不以其一国一家的利益为目的,而是要以天下万民之安乐为目的。于是,孟子放眼人寰,超越战国诸雄的国家局限,纵论古今,以天下苍生为系念,进而使他政治上的天下视野或者说“天下观”呼之欲出。
《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话,就代表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8孟子这段话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即战国诸王以嗜杀好战为能事,以攻城掠地为目标,不顾人民生计之困顿,缺失对大众生命的关爱与珍惜,出于一己之私而荼毒天下。并指出,这是战国时代一切政治问题和社会灾难的总根源。
然而,即使像梁襄王这样“望之不似人君”的战国君主,也希望消弭纷争,一统天下。不过,在此只能看到,善只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和愿望,却不是他们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和愿望而必须采用的主要手段。以战争征服来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孟子却不以为然,也不赞成这种认识和观点,指出战国君主们一统天下的方法是错误的。孟子认为以杀戮的手段来一统天下,只能成就恶的循环,因为它背弃了人民的意愿,在战国君主们无上威严之下,不可能建立起人民的真正幸福,只有推行仁政,怀柔天下,才能赢得天下人民的“心悦诚服”。这就是孟子为战国君主开出的治世良方,也是孟子天下观步入我们视野的最原初的形态。
在孟子这个最为原初的天下观中,超越群雄割据是第一要义,主张要赢得天下民心是第二要义,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须高度统一是第三要义。关键是孟子不认为实现善的目的必须通过恶的手段来达到,善的目的只有通过善的手段,才能产生真正的善的结果,形成一种稳定恒久的良性循环。
总之,孟子天下观的确立,体现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历史分野。这个时间历史的分野,也是春秋儒学和战国儒学的分野,更体现了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在理念上的重大差异。
二、孟子天下观开启了战国儒学的思想转换
孟子天下观出现于战国时代,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是儒学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天下观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问题中,为因应社会历史突变的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孟子是开启战国儒学思想大转换的先导者之一,因为在其后还有战国末期荀子的又一次儒学思想转换。
首先,孟子在战国时代推动的儒学思想转换,起自于三个最为决定性的客观因素。第一,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已不复存在,在春秋时代,由孔子所倡导的以“周礼”为仪轨的“尊尊之道”已无所依托,拥戴战国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也都不符合儒家传统“天下”观的标准和要求。第二,来自不同思想领域的较量和竞争日益激化,正如《孟子·滕文公》中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9百家争鸣的激烈震荡,使儒家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起而奋争,如其不然,则必然沉沦。第三,天下崩解,生民涂炭,儒家必须有所担当。在解民倒悬、力挽社会沉沦的危机中儒家也必须有所作为。正如《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本人所表白的那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0这就是孟子的境界和孟子的担当,也是孟子天下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其次,孟子天下观体现的是战国儒家思想的彻底转变,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孔子和孟子的思想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即孟子之儒学和孔子之儒学的不同追求和鲜明的时代意向。纵然如此,他们却有着在最高政治理想上的高度一致性,在思想原则上的高度契合性,以及在共同精神旨归上的高度统一性。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1的时代,也就是说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有着天下共主的时代,是一个尚有周代礼制勉强维系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回归三代盛世希望与可能的时代。所以,孔子的理想是“尊王攘夷”“克己复礼”,以为“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焉。”
孟子的时代则不同,这是一个“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12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天下共主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战国诸王各自为政,相互攻伐,无有已时,动荡和战乱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于是,孟子的时代没有了“尊王攘夷”的忧患,亦不像孔子那样对“礼崩乐坏”耿耿于怀,而是每每以“天下”来说事。在孟子看来,虽然没有了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但是“天下”总还是存在的。以“天下”来替代“天子”,以抽象来替代具体,是孟子主导的战国儒学思想转换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即是孟子儒学和孔子儒学的分水岭。
其三,孟子天下观的确立虽然源于其时代的政治现实,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孟子主动地回归于对时代现实的认知,敏锐而适时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孟子天下观是孟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也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更是被后世儒家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奉为最高政治理想的一个代名词,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3,以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4,这一政治担当精神与最高理想人格的思想源头。
我以为孟子天下观的产生,是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进步,理由有五:
第一,孟子天下观是在群雄崛起、周室式微之后,由列国分裂的政治背景中产生的。然而,追求统一,祈求天下安定,向往和平是华夏民族最为根本的民族性,这也是我煌煌五千年华夏文明延续不辍孔子的政治思想内容,虽历经磨难,仍能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之所在。第二,在失去天下共主的战国时代,虽处于列国纷争的乱世,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没有放弃或放慢追求天下一统的思考和步伐,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而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孟子天下观就是战国儒家所贡献的天下一统的方略之一。第三,在战国时代,华夏民族虽然失去了天下一统的安宁生活,但是华夏民族并没有被异族所征服,天下仍在华夏民族手中。所以孟子此刻以“天下”理念,来取代孔子时代以“天子”为天下一统象征的理念,则有着划时代的政治历史意义。第四,天下理念是抽象的,如果不赋予和指出其实质性的指谓和真正的代表者的话,孟子天下观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伟大的号召力。而《孟子》一书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人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人民是“天下”指谓的代名词,人民才是“天下”的真正代表者。何以为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答案。第五,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是其天下观的核心理念,也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相对于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思想认识水平,孟子这一思想的认识高度,已超越了陈腐而久远的历史纪年,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崇高精神依然鲜亮而光彩,具有一种难以跨越的思想高度。
把孟子天下观所蕴含的政治思想,与西周初期周公的“敬天保民”和“保民而王”,以及春秋时期孔子政治思想中的“爱人为仁”和“克己复礼”来对比,我们会发现,孟子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和他之前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主张,都已不在同一个高度之上了。因为在孟子那里,人民作为主体的社会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孟子天下观的这一政治主张,不比人类社会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本主义思想晚出。由此可见,孟子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也是最为远古的真正的人民思想家。
毫无疑问,孟子天下观代表了人民地位的空前提升,表明了儒家思想更加倾向于为最底层的人民发声,这也是儒家学说尤其是孟子思想,始终能够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也发现,苦难与沉沦固然会使一个民族饱受摧残,但它也能够使一个民族在精神上重新奋起。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苦难最为深重的时代之一孔子的政治思想内容,但正是战国时代造就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辉煌的思想文化,孟子思想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
孟子天下观不仅具有以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更为深入的思想层面上,还拥有富于批评和自我反思的重要功能。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长,都是从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中逐渐壮大起来的。以孟子为代表的战国儒家及其思想的转换,更离不开其积极入世、敢于批判、善于批判、深入反思的高贵品质。孟子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不是针对善良无助的人民的,而是针对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的。孟子勇于批判现实政治,尤其是对当权的最高统治者的批判,在古代政治思想流派中可谓首屈一指。
孟子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或自认为自己立场是正确的,而是出于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的那样,孟子一开始就指出梁惠王的认识错误,并以是非曲直为标准,通过充分的说理来加以证明,这在孟子理论思想的构架中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思想特点。孟子天下观中,把战国诸王和统治者作为反面对象来批判,甚至以嘲弄的口味来讽刺那些愚昧的当权者,并从对其的批判与讽喻中,提炼出自己的认识观点,这和庄子对现实的讽喻评价方式几乎是一样的。
可以说孟子天下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战国统治者的集体否定。在这一点上孟子和孔子看上去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是其用意的本质仍然是一致的。孔子否定的是“犯上作乱”的诸侯和卿大夫,因为他们是“礼崩乐坏”的始作俑者,是乱天下的罪魁祸首,而孔子的目的是在维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表达的是他“克己复礼”的政治初衷。
孟子否定的是战国诸王,认为他们是“率兽食人”的强盗,是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独夫民贼。甚至认为孟子天下观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问题中,“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16,并将人民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天下”情怀是以“民为贵”为结论的。可见孟子的天下观,最为显著的思想动机是以系念天下苍生为目的的。孟子面对战国乱世的严酷现实,天下纷争的政治现状,将战国诸王及其各自的统治集团,与全天下的人民进行了剥离,进而将天下归之于人民,把当权者划入了另类。这种剥离体现了孟子以另一种方式,又回到孔子原始儒学的最初道路之上,那就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和手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17。而孟子所谓的王事,就是他的“仁者无敌”的“仁政”与“王道”理想。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152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6页。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3页。
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0页。
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5页。
7.(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0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2-13页。
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55页。
1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9页。
11.袁梅:《诗经译注》,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02页。
12.(西汉)贾谊:《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13.(清)范能濬:《范仲淹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4.(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5页。
1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8页。
1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2页。
17.(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18.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66页。
1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0页。
2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1页。
2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1页。
22.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3页。
2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62页。
2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6页。
2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6页。
2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74页。
27.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页。
28.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4页。
2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01页。
3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79-80页。
3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80页。
32.杨伯峻:《孟子译注》,第79页。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学凯,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现代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与儒学研究。
本文由某某资讯网发布,不代表某某资讯网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chuangxinguoxue.cn/rujiasixiang/72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