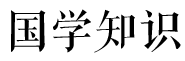从华严宗看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
从华严宗看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
一、从华严宗看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宗教同哲学不能够分开”。“离开哲学的智慧,宗教精神无从体验;离开宗教精神,哲学智慧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玄妙境界。”[1]他说就中国大乘佛教的六宗而论,密宗讲究修持,不立文字;禅宗讲究实际宗教经验,注重参禅。它们“虽然根据哲学,但是它本身还是可以同哲学划分开来”。而大乘佛学的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和华严宗,则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高度的哲学智慧。“这四宗佛学里而,哲学智慧的发展都达到最高的层次。”[2]而在这四宗之中,方东美又认为“华严哲学可视为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之大成”,[3]“华严宗系中国大乘佛学发展的最高峰”。[4]他将华严宗哲学视为中国大乘佛家哲学智慧的典型代表。
方东美所理解的华严宗的哲学智慧,主要表现在:
1、“理事圆融”的本体论
就宇宙而论,华严宗哲学消除二元对立,阐明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理事圆融。
方东美说:“华严要义,首在融合宇宙间万法一切差别境界,人世间一切高尚业力,与过、现、未三世诸佛一切功德成就之总汇,一举而统摄之于‘一真法界’,视为无上圆满”。[5]他也认为,华严宗以求得“一真法界”的“圆满实相”为理想,然而其立论之基础,却是极为平实的理、事关系。因此华严宗的宇宙论思想,可名之为“理想唯实论”。这一套宇宙论,可以分解为“法界缘起”、“法界三观”、“十玄门”、“六相圆融”诸要义,其中包含着“相摄原理”、“互依原理”、“周遍含容原理”(另一种说法是“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诸原理)。方东美在对这些要义和原理一一作出阐述之后指出,华严宗哲学以理、事关系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首先确定一个构成一切现实世界之所以形成的构成因素从华严宗看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也就是所谓的‘事法界’;然后再将一切的超越真相、一切的超越价值、绝对的价值、绝对的真善美,乃至于真相的圆满性、价值的美满性,都一一地令他们落到理性的这一方面去,这是属于‘理性世界’,又称为‘理法界’”。[6]这就是说,华严宗对“事法界”(现实世界)与“理法界”(价值世界)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但是,华严宗不将这种区分绝对化,而是提出了“理事圆融”的观念,认为“差别的事法界”、“统贯的理法界”、“交融互摄的理事无碍法界”、“密接连锁的事事无碍法界”都是宇宙本体“一真法界”的分殊表现,“理”可以摄受一切“事”,“事”也可以摄受一切“理”,因而并不存在“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理性与事实的对立”。理、事关系乃是一种交相融贯、互相对流、一体俱化的关系,可谓“事若无理不成,理若无事不显”。
华严宗“四法界”说的提出,使看似截然区分、相互对立的“事相”与“理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物的两面性”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显、相成、相即、相遍”的关系。方东美特别指出,“四法界”说所包含的“周遍含容观”(又称“互遍相资义”),是华严宗对大乘佛家哲学的重要贡献。他说:“‘周遍含容观’,谓观万差诸法,相融相即,以显真如理体,周遍含容,事事无碍。……准此类推,部分与全体,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无不相摄互涵。”[7]依照“周遍含容观”,诸多被视为相互对立的范畴之间,都是“相融相即”的关系。这就为人们观察“万差诸法”(囊括自然、社会、人生诸方面的一切千差万别的现象)提供了一种避免和消除“二元对立”观念的哲学原则。这样,“依据华严四法界的这一种观念,从关系的结构上,将可以把宇宙里而的一切二元对立性都一一地给沟通起来”。[8]这就可以消除那种否认“理”与“事”相互沟通、相融相即的“二元对立”观念。方东美认为,华严宗的基本思想一—“理事圆融”学说,反映了哲学思维中的一种“广大和谐性”,是中国大乘佛家哲学智慧的典型体现。
2、“内具圣德”的人性论
就个人而论,华严宗哲学昭示人人内具圣德、固有佛性,皆可顿悟圆成。
方东美说:“华严要义,……意在阐释人人内具圣德,足以自发佛性,顿悟圆成,自在无碍。此一真法界,不离人世间,端赖人人澈悟如何身体力行,依智慧行,参佛本智耳。佛性自体可全部渗入人性,以形成其永恒精神,圆满具足。”[9]他还进一步提出,正因为华严宗哲学以其“理事圆融”之说阐明了宇宙万法(包括人类)统统摄之于“一真法界”,统统不过是“一真法界”的分殊表现,因而华严宗得以证明人与“一真法界”相摄相融,人性与佛性相摄相融,或者说佛性渗入人性,人性包含着佛性。方东美还指出,华严宗这种人人皆有佛性的理念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强调人皆具有圣贤本性并且主张追求“圣德”正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他说佛学在传人中国之后,“随着时间之进展,不久即看出儒家思想中之种种优点,并发现其中与佛学思想在精神上有高度之契会:儒家当下肯定‘人性之可使之完善性’,佛家则谓之‘佛性’,而肯定为一切众生所同具者”。[10]佛家宣扬的“佛性”与儒家宣扬的“人性之可使之完美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正是佛家与儒家在精神上的融通、契会之处。
人虽然内具圣德、固有佛性,但要达到“一真法界”这个宇宙间“最神圣的精神领域”,则尚须自觉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身体力行,依智慧行,参佛本智”。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方东美将华严宗与小乘佛教作了对比。他说小乘佛学的缺点是只知道痛恨、诅咒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便认为现世的生命尽管有价值、有理想从华严宗看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但是这个理想无法实现。这样,小乘佛教自然只能使人把世界看成罪恶、黑暗、无知、痛苦的领域,认为理想的世界不在此生此世,而企图另求一个他生他世,从而放弃在现世中对于美好、神圣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而华严宗则明确提出“此一真法界,不离人世间”,虽然“一真法界”代表了宇宙间最高的“完美的极诣”,看似高不可攀,但人们只要自悟内在佛性具足、不假外求,向着美好、神圣的境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便可当下顿悟、圆成实性。
在中国大乘佛学诸宗之中,多有关于人人具有佛性、皆可顿悟成佛的教义,尤其是禅宗在这方而堪称突出。而华严宗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理事圆融”立论,“使诸差别心法,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显现为无差别境界之本体真如”,然后从这样的本体论看待人性,“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11]方东美认为,这种从“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到“内具圣德”的人性论的思想体系,表明华严宗具有极高的哲学智慧,中国大乘佛家具有极高的哲学智慧。
二、从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看道家哲学的影响
方东美认为,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主要是接受了道家哲学的影响。佛学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从传入中国到被中国人的心灵所接受,并且形成具有高度哲学智慧的中国大乘佛学,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的结合。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这就使得任何外来的思想,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当印度佛教经过西域传入中国时,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认可、接受的问题。方东美说,当时“西域的民族文化和中国关内的高度文化简直不能比”。[12]更何况在汉明帝时代,“佛教初到中国的时候,只是宗教的行动、宗教的礼节以及宗教的许多仪式。最初传来的总是有形的制度这一方而,但是有形的制度在宗教上,并不代表很高的哲学智慧。所以中国当时只是平民会接受,士大夫阶级就不肯接受”。[13]佛教仪式在当时甚至被中国的士大夫们斥为“淫祀”。佛教虽然传进来了,但是不能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里而生根,它缺乏与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灵的接触”。这种情形,直到公元二世纪才由于佛经的翻译而发生改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佛教思想实现了与中国哲学智慧的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拿道家哲学的思想精神,提升佛学的智慧”,[14]具体地说,就是“用道家的名词”、“拿道家的思想”去翻译佛家经典。

方东美主要从格义学的角度来说明道家哲学对佛学的影响。他说在当时的佛经翻译中,对于“格义”十分讲究,而“所谓格义之学,就是拿道家、新道家思想里面流行的名词,去翻译佛家思想里面的根本观念”。[15]例如,对于佛经里而的即“真如”,也就是宇宙最高的精神本体,康僧会把它译成“本无品”。“这是拿老子道德经里而本无的思想,去翻译佛教的所谓真如。”[16]魏晋新道家学说(即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名词是“贵无贱有”,它体现的也是道家的“本无”思想。当时的佛经翻译,就十分注意将佛经中的名词,与从原始道家到新道家一以贯之的“本无”思想相契合。“拿道家本无的观念道家的人生智慧,来说明佛家里而种种名词:如般若、本体、实际、法身,都是拿本无的思想去翻译。”[17]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从三国时代的支谦、康僧会到西晋的竺法护、道安、支遁、支道林,一直到苻秦时代、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都是用道家的基本名词,来翻译、解释佛家的经典。他们“一脉相承,皆力倡‘本无’,而视之为与‘真如’相通”。[18]道家的哲学智慧,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来自印度的佛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汉武帝、汉明帝以降,由于开发西域,打通了天山北路,而亚历山大的东征,从希腊到印度,经过波斯湾,也打开了到西域的道路。这就为当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通道。于是,当一些中国学者不满意传入中国的佛经时,便亲自去印度寻访原典。如朱士行,就先后带领一百多人西行印度取经,然后又导引许多印度佛学大师来到中国。像无罗叉、鸠摩罗什、觉贤(佛陀跋陀罗)等印度佛学家,就是从西域辗转经过天山北路,来到中国的长安等地。在长安,有两千多中国学者环绕在鸠摩罗什身边研习佛经。其中最为著名的“四大弟子”僧肇、道生、僧氰、道恒),都是“道家哲学修养最高的大学者”。鸠摩罗什和这些弟子们在一起,形成了当时中国佛学研究的中心。经过他们努力,不仅将初期佛经翻译中的一些错讹纠正过来,而且还进一步将中国道家的哲学智慧与印度佛学的宗教精神结合了起来。
“于是高度的中国文化,根据老庄哲学的精神,把外来的佛典美化了。然后再以老庄哲学结合外来的高度的宗教精神、高度的哲学智慧,在六朝之后的北方产生了佛学的般若学。这般若学就是智慧学,而表达智慧的语言文字就是老庄的哲学文字。……印度的大般若经,在中国同老庄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式的哲学智慧;这个哲学智慧,就是中国的大乘佛学。”[19]基于这种“道家思想影响佛学”的观念,方东美说具有很高道家哲学修养的道安、支遁、僧肇、慧远、道生等人是中国大乘佛学的创立者,正是他们“使佛学与道家哲学相接合(引者按:原文如此,疑‘接’系‘结’之误)而因以华化”,[20]从而成为中国式的哲学智慧。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大乘佛学的产生过程,从精神实质上说就是《大般若经》所代表的印度佛学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佛学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无疑接受了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外来的佛学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而成为方东美所说的“中国式的哲学智慧”的。方东美在其论著中,肯定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见之于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阶段,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见之于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他曾经指出,外来的佛学“仅仅接受道家的精神并不够,还要同儒家的精神也贯穿起来,这样才能够生根。因为中国整个的社会,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根本是一个儒家的体制。假使对于儒家的体制全盘不接受的话,要想在这里而成立体大思精的佛学那是不可能的”。[21]前文所述方东美关于佛家之“佛性”与儒家之“人性”相互“契会”的说法,也体现了他的这一基本见解。
但方东美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或者说更加强调的,则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此,我们暂且撇开如何全面评价儒家、道家思想对佛学的影响这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而思考如下一个问题:方东美为什么要强调佛学传人中国后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笔者认为,除了他所指出的道家哲学对于佛经翻译的影响这一“格义学”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方东美对于魏晋时期儒家与道家不同思想地位的看法。他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结果是“所独尊的儒术是把活跃创造的儒家僵化了”。[22]因此在他看来,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此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是道家兴起来了,成为一个新的精神。于是中国拿这个新的道家的哲学精神,去迎接外来的佛学”。[23]当时,何晏、王弼等“新道家”代表人物重新建立、发扬了道家的形上学,造成了“道家思想文化复兴”的局面。于是源于印度的佛教理论,实现了与道家哲学智慧的结合。换言之,在儒家思想衰退而道家思想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下,佛学自然主要是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个看法,再次反映了方东美对待中国学术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反对“独尊儒术”、“卫儒家之道统”的狭隘观念,提倡一视同仁地欣赏儒、道、佛各家的思想学术,包括他们的哲学智慧。
【注释】
[1]《中国大乘佛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67 页。
[2]《中国大乘佛学》道家的人生智慧,第267页。
[3]《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1页。
[4]《华严宗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上册第181页。
[5]《生生之德》,第311页。
[6]《华严宗哲学》,上册第494页。
[7]《生生之德》,第313页。
[8]《华严宗哲学》,上册第4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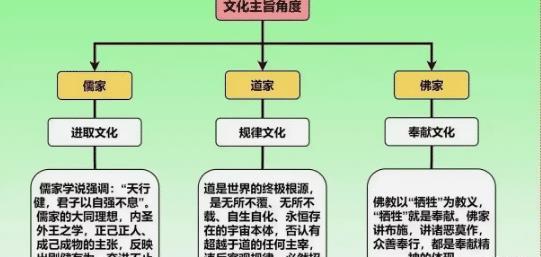
[9]《生生之德》,第311页。
[10]《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台湾成均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11]《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道家的人生智慧,第12页。
[12]《中国大乘佛学》,第5页。
[13]《中国大乘佛学》,第27页。
[14]《中国大乘佛学》,第33页。
[15]《中国大乘佛学》,第31页。
[16]《中国大乘佛学》,第28页。
[17]《中国大乘佛学》,第30页。
[18]《生生之德》第306页。
[19]《中国大乘佛学》,第23-24页。
[20]《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242页。
[21]《中国大乘佛学》,第41-42页。
[22]《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35页。
[23]《中国大乘佛学》,第22页。
(原载《江淮论坛》2004年第6期)
本文由某某资讯网发布,不代表某某资讯网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chuangxinguoxue.cn/daojiasixiang/3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