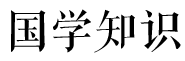胡适:秉承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与“率性”
长期以来,新文化的主要旗手胡适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的奉行者,反对孔子和儒家的急先锋。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生活在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胡适,与其他学者一样曾经受过多年的“旧学”(儒学)教育。儒家学说在胡适的思想内核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而且这种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
胡适对儒学的态度曾经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自从留学海外后,他拜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为师,还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家的学术养分。回国后,他曾一度赞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不久之后,他转而以更理性的眼光看待儒学。
儒家孝道观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当成“封建礼教”批判。但胡适在批评封建礼教的同时,又指出原始儒家的孝道观与后世儒家不同。此类认识在胡适对儒学的研究中比比皆是。他尊崇孔子与孟子的“真精神”,并将其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胡适不仅深受儒家“实学”影响,就连治学方法也不全是采用西方学术标准,还带有许多清儒治学的痕迹。
胡适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深受儒学影响,其为人处世也下意识地遵守儒家的君子规范。他在借鉴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同时,秉承了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到了晚年后,他的儒家思想特征越来越浓厚。
什么是“做圣”与“率性”?
一个学者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可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假如掩去姓名,读者说不定会以为某位学者不同时期的作品是两个人写的。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几乎所有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都会不断修订自己提出的学说,甚至推翻自己早年构建的理论体系。这种现象在胡适身上也出现过。尤其在他对儒家学说的看法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相对于梁启超等大学者,胡适的学术思想比较稳定,前后反差没到霄壤之别的地步。
胡适对儒家的看法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少年时代受家庭环境影响,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尊孔习儒;在美国留学之后,一度赶时髦坚决反孔批儒,但没多久就转变立场,以批判的眼光研究儒家学说,并高度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他在晚年时,无论为人处世还是价值观,都有着浓厚的儒家倾向。
罗志田教授曾用“做圣”与“率性”两个词来概括胡适的性格。“做圣”是传统儒者的人生目标。“率性”出自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原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直对胡适有着深刻的影响。
融新思想与旧道德于一身,是胡适的一大特征。他在文学上一直主张白话文,对文言文持否定态度。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激进的新思想。然而,他在行文写作时,往往又会替读者着想,生怕自己的文章不够通俗,不能被广大读者看懂。这种处处从细节上替他人考虑的作风,恰恰来自于其自幼打下的儒学功底。
胡适出生于晚清时的一个官僚家庭。其父胡传是秀才出身,对程朱理学略有研究,信奉儒家思想,参与过许多救亡活动。尽管他在胡适不满4岁时便去世,但留下了“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的家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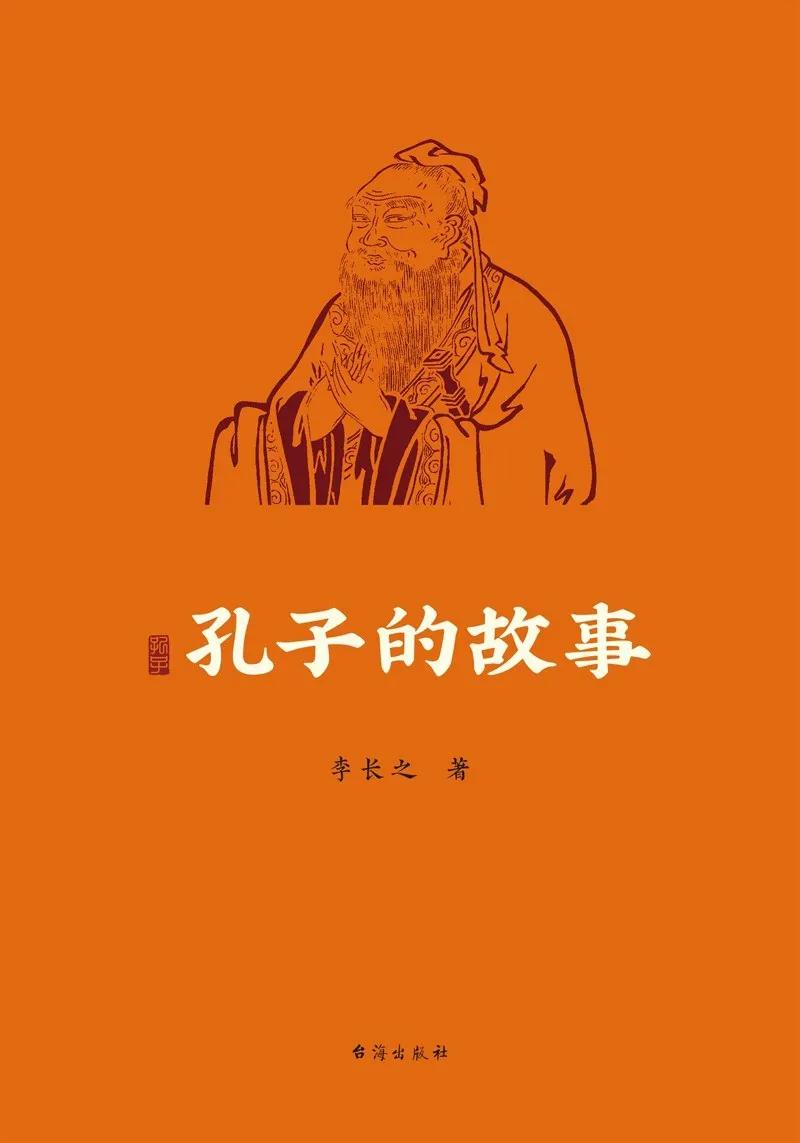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读了9年私塾的胡适,心中对儒家创始人孔子满是敬仰。据白吉庵的《胡适传》称:“胡适小时候不信鬼神,但对孔夫子是崇拜的……他找来一只匣子,做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个小匣糊上去,作为圣庙的内堂,堂上设有祭桌、神位、香炉等物,两边又增设了颜渊、子路等神位……每逢初一、十五,胡适便焚香跪拜。”
由此可见,胡适在少年时期尊孔尊儒,并有儒家士子“做圣”——实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人生抱负。
近代以来学贯中西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既是新思想的启蒙者,也被世人尊为最后的一批“大儒”。胡适从来不以儒者自居,自从留学美利坚之后,更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自己的主要思想内核。但他实际上颇得先秦儒家的精髓。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胡适,十分赞赏“仁以为己任”的孔子,称其为自由人文意识的开创者。因此,孔夫子“以仁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对胡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学派极其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致力于把每个人都改造成文质彬彬且仁义礼智信俱全的道德君子。有人将儒家主张称之为“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这种观点很对胡适的胃口。
胡适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比例来自西方文化。他鼓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甚至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时,也以此为衡量标准。根据他的总结,先秦儒家不仅有尊重智慧的苏格拉底传统,还具有强烈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唯理主义特征。这些恰恰是胡适最看重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在晚年才对孔子与儒家愈加肯定。
程朱理学与封建礼教让人们以为儒家是一个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恶毒学派。胡适身为“打倒孔家店”的主要倡导者胡适:秉承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与“率性”,也对儒家的阴暗面提出了尖锐而强烈的批评。但他并不否定儒家正源孔子的思想,而是认为程朱理学背离了孔子开启的自由人文意识与理智精神等优良传统。他性格中的“率性”成分,恰恰符合《中庸》的本意。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天然禀赋是“性”,顺着天性为人处事叫作“道”,顺着大道来修心养性叫作“教”。“道”是片刻也不能偏离的客观真理。可以偏离的东西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因此,有道君子在无人看到的地方照样谨慎做事,在没人听到的地方依然保持戒惧之心。
君子应当戒惧戒慎,时刻保持良好的道德修养。但“率性之谓道”,做君子不是做古板教条的机器人,而应该顺应天赋人性来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先秦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人情味恰恰与胡适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
胡适为人随和,讲话风趣幽默,时常逗乐众人。其秘书兼学生胡颂平曾经有几天没回家,胡适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脸对其开玩笑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当胡适发现胡颂平悄悄记录自己的言谈举止时,一度很紧张。但在他得知原委后,却大度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到了晚年时,胡适这种“率性”的性格仍然随时显露。
推崇《中庸》的儒家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虽然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定义并不完全等于当代学术语境下的“人性”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但其实践结果却是“终于在八百年来,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性,没有生气的中国”。
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他的头脑中深深扎根。这是胡适一度批孔批儒的主要原因。他反对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
他在《吴虞文录序》一文中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由上述内容可见,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明白无误地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然而到了1930年,胡适发表了一部长达103页的学术专著——《说儒》。这是一部借助西方学术理论系统研究儒学的专著。此书不仅标志着胡适对儒家研究的全面深化,也暗示了其对儒家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
在《说儒》中,胡适既不同于少时盲目崇拜孔子,也不再极端反对孔子,而是以批判的眼光理性地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自从发表《说儒》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提出过什么非儒反孔的言论。
胡适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曾说:“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关于“仁”的内涵,孔子在《论语》中给出的答案因人而异,有深有浅,看似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定义。但胡适指出,孔子所谓的“仁”就是“爱人”,是“尽人道”。他曾对冯炳奎、杨一峰说,孔子的“仁”说的是人类的尊严,“仁”之一字可以说是代表着真理。他还为孔子辩护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了路子,缠小脚、八股文、骈文,都是走错了路。”
从胡颂平所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中可以看出,晚年的胡适在言行举止中处处恪守孔子提出的“仁”与“礼”的君子规范。这位一生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在用大半生批判了儒学的糟粕后,依然流露出老式文人常有的儒家倾向。儒家的“做圣”与“率性”,则贯穿了胡适的整个人生。
胡适眼中的儒圣——孔子
儒家学说发端于孔子。无论后世的儒家各学派分歧如何严重,都将孔夫子视为最伟大的圣人。这个基本共识,也被胡适所继承。尽管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还多次批评儒教,但他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尊孔在当时的学术界并非新鲜事,新鲜的是胡适对孔夫子的定位。他经过周密地考证后,称赞孔子是一位人格十分伟大的儒家宗师。孔子作为殷商遗民后裔,超越了狭隘的畛域之见,打破了世袭贵族对儒文化的垄断,致力于将儒家思想推广到整个周朝天下。
在胡适看来,周王朝的统治阶级周民族,在文化上落后于商王朝的主体——殷民族。周朝建立之后,通过“损益”殷商的典章制度发展出自己的“周礼”。这实际上是一个周民族被殷商文明逐渐征服的过程。殷周两族的融合包含了自觉的方式与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方式是指两族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趋于“同化”。而“自觉”的方式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主动向诸侯与士民推广源于殷商文化的儒学。
按照胡适的研究成果,“儒”原本是殷民族的“祝人”(负责祭祀的官员)。商周文化不同,故而旧“儒”学长期以来仅限于殷民族内部传播,并不是天下列国普遍认可的思想文化。
孔夫子的杰出贡献在于,把“儒”的范围扩大化,让“儒”从殷民族的祭祀者变成了全国上下的传道授业之师。胡适认为这个转变标志着“儒”的中兴。被放大后的“儒”学,不再局限于殷商遗民的小圈子,而是可以与周文化及各诸侯国文化相兼容的新思想资源。假如没有孔子的改革,殷周两族的文化融合也许会演变成另一副模样。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境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所以他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
殷商遗民往往更欣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为周文化比较落后。但孔子没有被这种畛域之见所束缚。他公然宣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周朝继承发展了夏商两朝的礼乐法度,已经达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境界。所以,他选择尊崇周朝的礼乐文明,并终生致力于恢复周礼。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西周王朝已灭,历史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心中的周文化,并不是武王伐纣时周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而是承袭夏商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周文化。这种周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殷商文化的成果。
胡适曾论证道:“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日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目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地呈显出一种‘集然大备’的气象。”
因此,孔子所谓的“从周”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个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周文化。他将殷商旧“儒”学与周文化充分融合,发展出了后来的儒家思想。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绝非盲目“从周”,而是根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对殷周文化加以梳理完善。应该说孔子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发展潮流,自觉革新了“儒”的定义与内容,从而使儒文化获得了新生命。
为了弘扬革新后的儒文化,孔子将目光放在了全天下人身上。当时贵族垄断着教育资源,庶民阶层往往缺少读书机会。但孔子却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在孔子看来,教育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可以打破一切富贵贫贱的界限。他主张“有教无类”,宣扬平等的教育观。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观念。他的学生既有出身尊贵的鲁国公孙,也有被社会鄙视的商人胡适:秉承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与“率性”,还有极度穷困的贫家子弟。孔子门下的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被称为“贤人”的就有72个。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诸子百家私学陆续兴起,与孔子打破教育垄断传统不无关系。
胡适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根源于其对“仁”的追求。仁者,人也。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总根源。而孔子在《论语》中动辄提及“仁”字,可见其将“仁”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教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学生曾经多次问“仁”的含义。孔子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位学生讲解。但他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每次都给出不同的回答。
孔子对樊迟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切。为之难,言之得无功平?”
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
对仲弓说:“(仁就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公。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以上回答阐述了不同层次的“仁”。在胡适看来,孔子的“仁”其实就是“做人”。他点评道:“用那理想境界(仁)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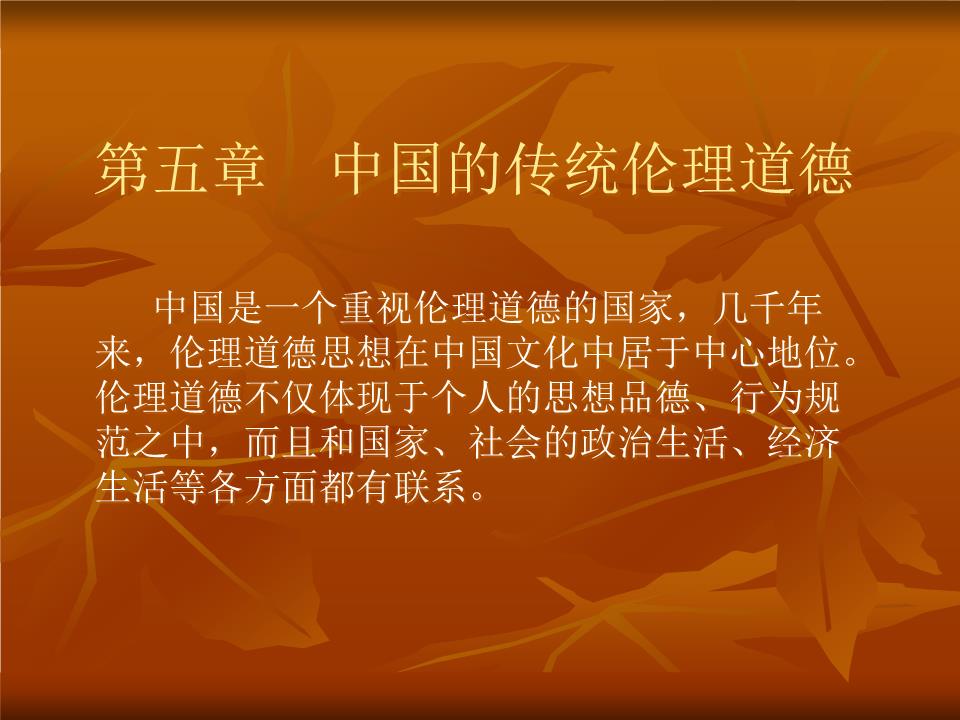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与过去的殷民宗教“儒”相比,孔子的师“儒”没有亡国遗民那种柔懦的作风,而是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以及进取心。孔子对自己领导的文化教育革新运动十分自信。他认清了殷周民族六百年来逐渐同化的文明发展趋势,对弘扬正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仁以为己任”的孔子秉承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由此可见,孔子将原有的“儒”与杀身成仁的尚武精神整合成一种新的“儒行”。这种新“儒行”以“成仁”为主要目标。
此处的“仁”,实际上将当时社会上各种杰出人物身上包含的美德融为一体,锻造出一个理想君子的模板。但孔子只是将其作为最低标准的信条。据《论语》记载,孔子曾经自谦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的学生子贡则称赞曰:“夫子自道也。”由此可见,担当天下重任,坚持不懈地弘扬儒家正道,是孔夫子终身追求的理想人格。
因了此故,胡适在晚年将孔夫子比作古希腊著名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他早年曾经是“打倒孔家店”的代表性人物,但对孔子却有着一种莫大的敬意。说到底,他把孔子看作是古中国自由精神的代表,让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苏格拉底传统。
胡适眼中的儒家发展史
不同于传统的儒门经学家,胡适的治学方法吸收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中西合璧的学术功底,使得他能站在一个不同于旧式大儒的角度来评价儒家学说。胡适运用西方学术理论的眼光,对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研究。这开启了中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一大先河。
胡适认为,“儒”最初是周朝殷商遗民中的“教士”。他们穿古服,行古礼,不事生产,甚至乞食于人。由于熟悉礼乐祭祀,“儒”扮演着重要的宗教性角色,以自己的知识作为“衣食之端”。但孔子的出现,让“儒”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孔子是殷商遗民后裔,熟悉礼乐。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殷周文化经过漫长交流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将“儒”从殷民族的祭祀官员转变为全国人的儒师。
在胡适看来,孔子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儒学中兴,是殷商遗民文化运动的新高潮。经过孔子改造的儒学,成为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孔子超越了殷周的畛域之见与贵贱的阶级观念,致力于向全天下推广儒家思想。在他的改造下,儒者不再奉行柔懦恭顺的亡国遗民式人生观,而变得极富救世情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刚健品格兼济天下。
胡适从哲学的角度将孔子的“仁”定义为教人如何做人,将儒学看作一种教育人如何为社会做贡献的学说。这里面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儒家要求每个人以不断地学习思考来修身养性,从而保持高贵的人格,活得更有尊严;其次,儒家要求儒者在社会实践中推广“仁”,使之成为保持社会安定及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利器。
在胡适看来,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儒家有教无类思想将芸芸众生一视同仁,推行仁义,无论尊卑贵贱。按照这个主张,上至君主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应该以谦虚谨慎的态度钻研学问,以“士不可不弘毅”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从而实现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对孔子思想的认知,是以现代社会人文观念为基础的去芜存菁。
被后世书生尊为“亚圣”的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儒家大宗师。在他的努力下,儒家虽不为战国诸侯重用,却依然发展为影响力极广的天下显学。
胡适对孟子的仁政哲学有着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孟子比孔子更加关心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利。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贵君轻”理论。胡适据此认为孟子的学说对百姓的尊重超过统治者,体现了让百姓享受乐利的思想。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民本主义观念。
荀子是与孟子齐名的战国儒家大师。荀子经常批评孟子,其学说又包含了浓厚的法家色彩,故而后世儒家学者对荀子的评价不高。
胡适站在现代学术的角度,对荀子的哲学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荀子学说与孔子的人事主义一脉相承。荀子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与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精神殊途同归。此外,胡适还将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解读为一种征服自然的观点,并与英国思想家培根的“戡天主义”进行类比。
西汉大儒董仲舒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对儒家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胡适认为,正是董仲舒让儒学发展走上了歧途。
董仲舒的儒学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学说为哲学基础。胡适认为,此举标志着儒学开始宗教化,故使其在百余年发展中演变成了恐怖迷信色彩浓厚的怪诞学说。直到东汉时期,新兴的古文经学才修正了这个弊端。
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在古文经学家中,胡适最看好的是激烈批判董仲舒的王充。
胡适认为,人文精神是儒家的一大精髓。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将阴阳神学融入儒学,完全背离了儒家最根本的人文精神。而王充猛烈抨击董仲舒及其追随者的灾异符命思想。胡适声称:“(王充)这一批判是用人的理智反对无知和虚妄、诈伪,用创造性的怀疑和建设性的批评反对迷信,反对狂妄的权威。大胆地怀疑追问,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正是科学的精神。”他还将王充的举动抬高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洋溢着批判精神的思想运动”的文明高度。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不同的是,王充借鉴了道家老子的自然主义宇宙观。按照胡适的观点,王充融合了儒道两家精华,其思想是道家自然主义与儒家人本主义的结合。这不仅发扬了孔子以来的人文精神,还通过怀疑与批评天人感应论,为儒家注入了理智精神的新鲜血液。故而胡适认为,自从王充发表《论衡》之后,中古社会的思想意识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儒家在东晋时进入了一个低潮期,遭遇佛教和道教的强力调整。哪怕到了人人称颂的学术风气比较宽松的盛唐时代,儒家的整体发展状况也不尽如人意。
胡适对这个阶段的儒学评价很低。在他看来,孔子开创的自由人文意识在当时遭到了世人冷落。先秦至两汉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严重缺失。胡适认为,在此期间,唯有韩愈的“反佛振儒”运动是令人敬佩的亮点。
韩愈在佛教狂潮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精神。他在《原道》一文中宣扬“反佛振儒”的主张,呼唤人性的回归,通过排斥佛教来恢复中国古代的唯理哲学。在胡适看来,如果没有韩愈的力挽狂澜,儒学将难以摆脱发展的桎梏,整个思想体系可能会滑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70%
本文由某某资讯网发布,不代表某某资讯网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chuangxinguoxue.cn/rujiasixiang/6826.html